Piotr Ilich Tchaikovsky
1840-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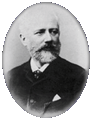 柴科夫斯基生在俄罗斯一个边远省份里的沃廷斯克,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他十九岁时毕业于彼得堡的法学学校,并在司法部供职。二十三岁时他辞去公职,进了新成立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三年就完成了学业。校长安东·鲁宾斯坦推荐他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勤奋地致力于作曲,创作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柴科夫斯基的性格敏感,草率的婚姻又加剧了他的不幸,几乎要使他精神崩溃。这时一位仁慈的女赞助人梅克夫人出现了。她资助他到国外去,直至恢复健康;也使他摆脱了教学工作,开始了一个多产的创作时期。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通过通信结成的友谊。此后,柴科夫斯基的名声逐渐传开了,他成为第一个以其音乐吸引了西方趣味的俄国人。他在最后几年的通信中吐露出他不再报有幻想,怀疑自己不再有东西要表达了。但他还是创作出两部最好的交响曲。在他刚刚完成《第六交响曲》即《悲怆》时,突然染上霍乱去世,时年五十三岁。 柴科夫斯基生在俄罗斯一个边远省份里的沃廷斯克,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他十九岁时毕业于彼得堡的法学学校,并在司法部供职。二十三岁时他辞去公职,进了新成立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三年就完成了学业。校长安东·鲁宾斯坦推荐他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勤奋地致力于作曲,创作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柴科夫斯基的性格敏感,草率的婚姻又加剧了他的不幸,几乎要使他精神崩溃。这时一位仁慈的女赞助人梅克夫人出现了。她资助他到国外去,直至恢复健康;也使他摆脱了教学工作,开始了一个多产的创作时期。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通过通信结成的友谊。此后,柴科夫斯基的名声逐渐传开了,他成为第一个以其音乐吸引了西方趣味的俄国人。他在最后几年的通信中吐露出他不再报有幻想,怀疑自己不再有东西要表达了。但他还是创作出两部最好的交响曲。在他刚刚完成《第六交响曲》即《悲怆》时,突然染上霍乱去世,时年五十三岁。
很少有作曲家像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那样能代表十九世纪末的情绪。他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看到自己的信仰已经破灭,而且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表现了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最后阶段的悲观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说:“他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彻底的俄罗斯人。”在同胞的眼里,柴科夫斯基是一个民族艺术家,在他的音乐中他把俄罗斯的因素摆在很有分量的位置上。“因为简朴的俄罗斯风景、夏天漫步在俄罗斯田野和森林里,或是晚间在草原上的散步都能感动我,我会被一阵热爱自然的思潮所攫服,茫然的躺在地上。”同时,在创作音乐时,柴科夫斯基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被意大利歌剧、法国芭蕾舞、德国的交响乐和歌曲迷住了,他把这些都吸收到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而继承来的民间旋律中,并在这种混合物上打上了个性鲜明的印记。 |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从不关涉重大社会问题,他的想象力总是脱离现实生活,而沉溺于虚幻的世界里。然而从青年时代起,他那敏感脆弱的性格,就深切地感觉到现实社会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的怀疑主义和他那宿命论的思想,使他在落日的余辉里孤寂地去寻找对人生的妥协。音乐成了他蜗居斗室自我拯救的唯一生存方式。
艺术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似乎已是老生重谈。意大利精神病学家Lombroso
Cesare在1864年指出在大音乐家中患病的特别多,包括妄想与幻想综合症、抑郁症和狂躁症。翻阅一下柴可夫斯基的书信和日记,我们便不难发现,柴已经不是自卑、自贬,自我丧失的问题,而是要结束自我。在柴可夫斯基一生中,几次精神崩溃时都想到了自杀。在令人厌烦的社交活动中,抑郁会象鬼魂那般死死地与他纠缠。这种性格自然会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这种创作心灵完全来自与病态的不安和沮丧。每逢这时,他总能写出一些眼泪汪汪的调子和伤感情怀的旋律。或是沉入类似“冬日梦幻”那种虚迷境界中,任自己的感情之流迷走飘逸。这种又酸又苦的忧伤和哀愁,影响了他中后期的许多作品。然而,抑郁症在某种情形之下,会转化为与与症状完全相反的狂躁症倾向。这种反差极大、两极摆动的精神断裂、间接造成柴可夫斯基音乐中的许多断裂。很多作品中的一些优美旋律,常常被粗暴所打断,接踵而来的往往是跌跌撞撞、迅疾跳跃的不稳定音型。过去的评论家只认为他不善于构造交响的逻辑大厦,只是听凭他的情绪系列的相互交替,而且把这种交替变成是一种性格上的对比。实际上,这并不是音乐结构的问题,而是音乐家的心理程序对作品程序的一种投射;是一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段裂,而非局部和局部之间技巧性的衔接问题。尤其是在他晚年作品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那种响亮中的空虚,那种紧张中的惶恐,那种狂躁中的沮丧,那种虚假镇定中真正的绝望!
本世纪80年代一位从前苏联柴学研究者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爆炸性新闻:由帝国学院组成的一个“袋鼠法庭”对柴可夫斯基宣布的一项“判决”的受害者,并非象官方报道的那样死于霍乱。该法庭根据一位地位显赫的贵族给沙皇的控告信,认定了柴可夫斯基引诱那位贵族老爷的侄子搞同性恋的罪行,从而判决让作曲家服毒自杀。这件19世纪音乐史上最令人震动和悲惨的丑闻使得举世震惊。
伟大艺术家中的同性恋者为数不少,但丁的老师拉梯尼,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英国诗人马娄,剧作家王尔德,哲学家培根,英国伟大诗人蓝波以及奥地利作曲家马勒都在此行列之中。如果说奥尔罗娃的披露还不足以完全认定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的话,不妨让我们在此稍作一番精神分析的心理论证。一般来说,同性恋者有时会突然冒出结婚的念头来,他(她)们想以此作为一个治疗的办法。但这种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让我们来看一封作曲家1876年9月22日写给弟弟莫德斯基的一封信:“从今天开始,我将设法结婚,正正经经的和某人结婚。”还不知道自己的恋人是谁,没有在异性的身上感到一种青春的勃发和不可抵御的性爱诱惑,便异想天开地要设法结婚,这难道是正常人所想所为的吗?事实上,他和他的学生安东尼娜短暂的失败婚姻提供了最好的佐证。柴可夫斯基时时处于神经衰弱状态,或者处于性方面的精神衰弱状态。他有时敏感、多情,有时焦虑、恐慌。这种状态几乎跟了他一辈子。得不到异性之爱的他
,只能靠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极少数的几个朋友,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内,他一生中和弟弟有大量的通信,他向他们倾诉自己内心的郁闷与痛苦;他这个孤独的单生汉经常把妹妹的庄园当作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之一,并在那里写下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
结婚是一个悲剧,与弟、妹的情感又不能长久依赖,如何能让同性恋者的柴可夫斯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精神家园,而不再饱尝精神的颠沛流离呢?于是有了梅克夫人。正是同这个有知识,教养的异性保持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才使他有了生存和创作的精神支柱。(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这种方式对同性恋患者的治疗更有益)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集中,这种超乎肉体的精神恋情随处可见,而且随着他们的交往而且日益加深。1890年9月在收到梅克夫人的断交信后,柴在复信中写到:“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疯且毁灭。”从此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精神果真全面彻底地崩溃了。梅克夫人是他心中的上帝,她突如其来的绝交从灵魂上陷柴可夫斯基于死地。在“悲怆”中,柴可夫斯基已经为肉体自杀作了一次精神自杀的预演。他绝望地在这部辞世之作中凄凉地走完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大起大落、大波大折的旋律中,有对遥远的过去的甜蜜回忆,家乡的空气,母亲的呼唤,兄弟的情谊以及梅克夫人那天使般的精神之恋......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抑郁到狂躁的情绪在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当残酷的命运把他交给死神时,千疮百孔的灵魂已疲惫无力。在最后的乐章中,心灵最后一次面对自我,最后一次经历着人生大悲的痛苦,生命颤抖着走向死亡。
|
|